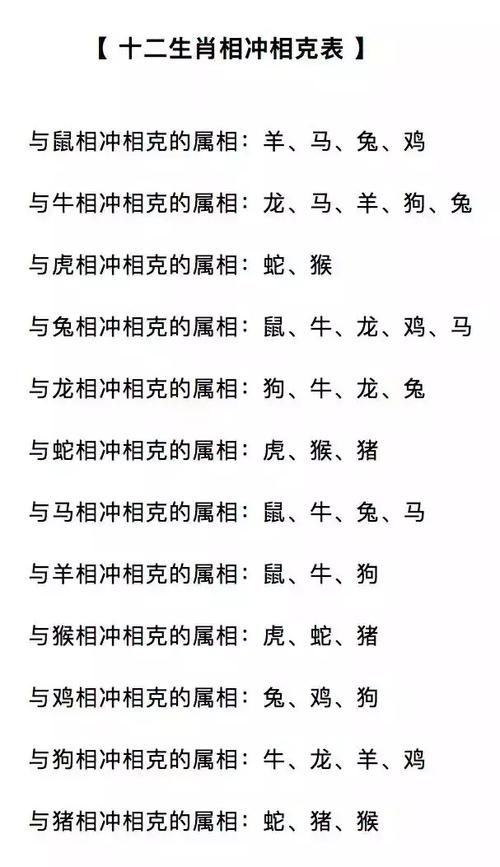1973年生肖属蛇 1973年属蛇2023年运势及运程
(一)
时间的马车跑进1973年春,史安坪来了个女知青。她叫杨百合,女孩体形瘦弱,看人的表情略带忧郁。这模样不算什么,可久处寂寞的我,就像看见了西施浣纱,亦或希腊美女海伦走错了地方。我从她瘦削的肩头,看到了久违的古典仕女之美;及至腰间的曲线,呈现小家碧玉流水般的温柔。总之忽见这样的女人,可以使人相信理想、爱情,甚至希望。
“听说你下乡三年了,总在使劲?”那天我们见面,女知青问。
“是呀,三年了。是诗经,有两千年了。”我有点紧张,语无伦次。
“诗经我知道,那有何用呀?”她似在笑问,嘴角却向下弯曲。
“看山太静了,就为弄出点声音。”我嘀咕,想不出更好的理由。
“难怪哦,社员都叫你疯知青……”她的语气,如同六月飘雪,使我从头冷到脚跟,但不甘心,嘀咕道:“疯不疯的,只要我喜欢,就不放弃。”我似在说诗,其实在暗示心仪。女知青“唉”了一声,转身走开了。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决心把这事儿搞下去。
以后我照样巡山,也常见女知青与社员下地出工。当时那地儿,我们没有所谓知青户。史安坪共有九个生产队,知青都散居在各处的深山里。我穴居在四大队的东南坡,女知青住在一个叫“烂泥湾”的斜坡下。我们相距不远,即使偶有见面,她不冷不热,总是说:“知青接受再教育,要注意影响……”
直到有一天,我逮住了几个伐木贼。因是群体作案,公社予以表彰召集知青开会。那场合,与会者掌声稀落,但见杨百合向我走来。她祝贺我,然后问:“看青好玩么?”我说不好玩,她笑道:“听社员说,看青会遇到有趣的事儿。”这话使我想起“偷青女”的鬼把戏,赶紧转移话题:“也没趣儿,所以我背古诗。”女知青要我背一首,我随意选了“邶风静女”一节,吟道:“静女其姝,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……”
我说这是古代男女幽会的场景,她说:“静女其姝,这名字好美。”我告诉她,邶风是先秦诸侯封地的一首民谣,诗中展现出古代男女幽会的场景。我说这是我读诗经以来,感觉最美的古代情歌之一。我希望杨百合能听出其中的寓意,但她的脸上毫无表情,低声道:“既是古代情歌,面对现实就不合时宜。”她说话时不看我,然后又走开了。
实际上,相对于我的冷漠,女知青对农民却非常热情。她常去社员家串门,还帮做家务,带看孩子。她送给社员肥皂牙膏,送村姑塑料花。有一回农户嫁女外县,她充做伴娘,随同送亲队伍爬山涉水,摔得鼻青脸肿。女知青如此殷勤,但是遇到力气活儿,她并不要求社员帮助,反而有求于我。
一天下午,杨百合要我帮她收拾晒场的小麦。这是队里分给她的口粮。烈日下,我用连盖将小麦扬壳,然后装袋背去机房磨粉。忙活下来,麦芒刺的我浑身难受。我想去找个水坑游泳,她说天很晚了,让我去她家洗洗。她穴居的地窝比我的还小,不过窝门是用厚木板做的。我弯腰进去,看见一个灶台,周围堆放着农具和杂物,都收拾得很整齐。窝内有张小床,床单被褥干净整洁。床沿上有笔记本,几本红书,还有一盏小油灯,擦得锃亮。
女知青打来一盘水,递给毛巾和肥皂。我擦洗身子,找话说:“自从你来到史安坪,好像我的生活都变了样。”她问变啥样呢?我无言以对。她倒掉脏水,另换一盆清水准备自己洗。女知青把衣服纽扣解到第二颗,侧身说:“我想洗洗睡了,你也请回吧。”我有好多话没有说出,悻悻地走出。我看见初升的月亮,对自己说:“就算一厢情愿,我也要把这场爱情进行到底。”
又一个下午,女知青过来说她的烧柴没有了,要我帮她去山里砍柴禾。这事儿我知道,按队里分配,知青的柴禾都划分在较远的山里。她说:“路太远,背不动。”我二话不说,拿上砍刀和绳子和她上山去了。砍柴中我的手给荆棘扎了,很有些痛。女知青从头上取下个小发卡,试图用它来挑刺。我告诉她去树丛找一根较大的刺儿,用它来挑就行了。女知青“哦”了一声,遂去荆棘丛中掰下一根大刺。她握住了我的手,开始挑刺。或因近黄昏,视觉很昏暗,结果弄得满手是血,但我并不感觉疼。
女知青个儿矮,只顾埋头找刺,我就看见她的脖颈了,洁白而修长,在夕阳下泛出白玉般的光芒。我不禁附下身去,呼吸急促。她大概感觉到了颈后的热浪,猛一抬头,惊问:“你干什么?”我赶紧伸直腰,嘀咕:“嗨,别挑刺了。我们还是回吧。” 我将砍下的柴禾捆扎好,扛在肩上,往下山走去。返回途中,我俩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。
我的暗恋,直到次年冬天才有了转机。那是在最冷的二月,一天夜里,我听见地窝门的栅栏有响动,以为是山里的野物闯入。我拿起一根木棒,移开栅栏,没想到进来的居然是杨百合。我点亮油灯,看见她头发凌乱,脸色惨白。我惊愕地问怎么啦,她直喘粗气,带着哭腔:“妈妈来信说,我爸死了。我想回去奔丧,可是敖头不批准。他说我爸是畏罪自杀,要我划清界限,站稳阶级立场……”一听这事儿,我就知道很麻烦。
女知青哭诉道:“就刚才,我又去求他。敖头他,突然对我动手动脚。我拼命挣脱,就跑你这儿来了。”她说的敖头,史安坪的知青都知道,是公社专管知青工作的下派干部。此人约40岁,五短身材,知青都叫他“骚棒”的绰号。他凭借手中的权利,刁难下乡知青,尤其经常欺侮女知青。
“那骚棒!他把你怎么啦?”我怒问,女知青没有作答,但在昏暗的油灯下,我看见她的里噙满了泪。我不想知道这事儿有多糟,说:“他敖头不批,你就自己走嘛。”女知青突然放声大哭:“自己走,我哪敢呀!敖头说了,反动家庭不论成分,重在政治表现。我是黑五类,表现不好,就别想离开这儿……”她哭得噎气,说不下去了。
“那么,我去和他说。”我一时血涌,抄起柴刀走出。杨百合一把抱住,喊道:“你别去拼命呀!这不值得,总有办法……”我俩僵持了一会,她说邻队有个知青也有类似的遭遇,给了敖头二百元,事情就解决了。我说这也行呀,可她又说家里很穷,父亲死了,妈妈还病着……那时节,她紧抱住我,浑身颤抖。那年冬天出奇的冷,冷得好像不是在人间。我也在发抖:“我不忍看见,你在受苦……百合呀,因为我爱你!”就这样,在这幽暗的地穴,一个奇冷的寒夜,我终于对她表达了爱情。
“爱情么……”杨百合好像陷入了沉思的深渊,过了好一阵才说,“天禹你可知,在这里,我也无时不感到孤独和恐惧。”她这话是同意,还是拒绝?我仰望星空,一片漆黑。我低下头去,第一次亲吻了她,时间好长,长得如同在另一个时空。
(二)
我们似乎相爱了,但又并非事实。杨百合要求保密,而且不能发生关系。我表示理解也感到沮丧,原来男女之爱,是无须写什么诗、唱歌什么的,没那么浪漫和神圣。我过去所受的情感教育,自恃的爱之情操,在这地儿只能像做贼一样。
一天夜里我问她:“我们这样子有爱情么?”她的脸上仍无表情,我又说史安坪几十个知青,也有谈情说爱的,都光明正大。她神情忧郁地说:“我怕怀孕,更害怕敖头看出来。”我指出这是自由恋爱,和那混蛋没关系,她却说:“妈妈在家等我。我要回家,不想永远留在这里。”我无语了,陷入尴尬和沉默。
“我俩这事儿,还是到此为止吧。”她忽然说,“这种事要想不为人知,除非己莫为。天禹你可知,因为当时的我,深感无助和绝望,也需求安慰和帮助。所以现有的状况,不是爱情,那会把我一生都毁了……”女知青顾虑重重,泪如雨下。我勉为其难,其实心里明白,所谓爱情是不存在的,真正的渊薮还在于:杨百合出身不好,要维系下乡的良好表现,尤其女知青比男知青更艰难。我不知道她的父亲究竟是右派、特务、还是资本家(她从不和我说这事儿。)但是那年头,只要摊上其中一种家庭成分,其子女就够倒霉的了。
我也够倒霉的,好不容易得了爱情,刚开始就结束了。更何况那骚棒还在纠缠,竟也批准了女知青回家一趟。她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,我不得而知,也不想过问。我只是揣测,但愿这里边有没有罪孽。实际上,女知青省亲回来后,就不再理我了。但是我的“荷尔蒙”在堆积,眼见心仪的女人遭损,作为一个正常男人,我虽然没有狗胆与之较量,但也不妨色胆包天的想出一个办法来。
一天傍晚,我假借汇报“活思想”的机会,把敖头诱上山。我们转到一片果岭,当时正值桃子成熟期。我给专管干部展示“再教育”的丰硕成果。敖头面带喜悦,随手摘下一个大桃,吃得满嘴流汁。也就在这时,我发出了“快追”的指令。我那狗早就看不下去了,只见它狂叫一声,扑倒了敖头一顿乱咬。狗子扯破了骚棒的衣服和裤子,就在要咬破他的卵蛋之际,我赶紧叫停:“嗨,住口!”这情节在今天或叫犯罪中止,可那会儿算个屁。
那可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,但见受害人昏倒在地,衣服撕破了,却也没什么血迹。其实狗子咬人不凶,他多半是给吓昏死了。我抓住他使劲摇晃、喊叫:“哟喂!我那狗呀,以为你偷窃集体财产。所以咬人,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……”敖头好歹苏醒过来,脸色铁青,肺都气炸了:“好小子,你纵狗行凶!你竟敢,残害国家干部!”
事发当晚,敖头召集民兵召开批判大会。人们燃起火把,振臂高呼:“把疯知青,押上来!”我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,敖头义愤填膺、罄竹难书,当即对我拳打脚踢。我被揍得晕头转向,鼻血长流。更气苦的是,平日关系不错的社员也冲过来,对我连续扇耳光,打得我鼻血长流。这也难怪他们,如果不打,干部不会给他们好日子过的,何况我也曾偷过社员的菜地和鸡鸭,活该挨揍。
那阵仗,我透过如林的拳头,看见女知青在下面抹眼泪。与此同时,我听见狗子在拼命狂叫,它狂吠仅仅是为了护主,当然不知道人类发生了什么事。然而人狗相见,敖头分外眼红,当即责令民兵予以扑杀。狗子听见枪声,一溜烟跑掉了。民兵追杀了三天,没有追上。后来狗子蹑手蹑脚地回到主人身边,我抱住它悲喜交加,但也没有哭。
事已至此,我便成了史安坪的“坏知青”典型。因为我让邻队女人偷青已被查处,定罪监守自盗、破坏生产。此外,我与杨百合的爱情也被查出,至于定性“通奸、还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,有关领导正在罗织罪名。那年头,搞臭一个人很容易。
事后女知青怕得要命:“天禹呀,幸亏那狗没咬死他。不然你就完了,我也完了。” 她说得很悲切,不过这话也说对了,我们的“爱情”也就此彻底结束了。以后偶有见着,两人都视同路人,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。接下来,敖头解除了我的看青活儿,派我去玉溪河打石头、伐林木、炸高山修大寨田。活儿又苦又累,我由此学会了石匠和爆破。这手艺在我后来的生计中,远比背诵《诗经》更有用。
时间到了1974年,那时候已经有学校、工厂来农村招生、招工和征兵,并通过文化考试予以录取。知青们开始温习旧课,拼命看语文、做算术,都妄想通过文化考试离开农村。在大家拼学返城的热潮中,都认为我最有希望。实际上第一轮考试,我的语文算数都及格。可不幸的是7月出了个“交白卷”的英雄人物,此大事连中央都知道了。这样一来,知青调遣仍以领导审核为主、社员推荐为辅,文化知识屁也不是,个人表现越发显得重要。
那是一个极其难熬的夏天,我经常远远看见,敖头与女知青在田间地头促膝谈心,男的手捧红宝书、循循善诱;女的紧握黑钢笔、认真笔记。他们每每谈到夜幕降临、妖雾弥漫,我啥也看不见了为止。我就想,那天真该让狗咬掉他那玩意儿。不过到了10月底,经社员推荐、领导批准,杨百合要上“工农兵大学”去了。我感到欣慰,可怜的女人历经磨难,如愿以偿;至于为此付出何等代价,我不想赘述,只能说这就是一代人的命运。
但是我俩毕竟初情一场,按照知青调离惯例,应该给她做一个饯行。可吃的还没有,我去夜袭农民的菜地,偷得白菜、萝卜,但是没有肉,好在田沟里的黄蟮多(当地人不吃那东西)。我扎了一个火把照着,捉了不少青蛙、黄蟮,还抓了一条蛇。女知青不吃蛇,我将它放了生。晚上我煮了一锅大杂烩,因为没有油,腥味扑鼻。我们蹲在地上吃,也许女知青吃了肠胃不适,竟以为我在饭里放了毒!
当事时,我饯行的祝词还没说出,女知青已经表情凝重,面色死灰了。接下来的十分钟里,她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,继而呼天抢地:“救命呀!来人啊!乡亲们啦……”夜半呼声飘出地窝,把农民大伯、社员婆娘都引来了。人命关天,大家惊慌失措,有说赶紧叫赤脚医生,有说先把男知青捆起来。男社员立刻找来绳子,跃跃欲试要捆人。女社员忙着给女知青猛灌淘米水,搞得女知青呕吐不止,快翻白眼了。最后赤脚医生和社队干部都来了,他们探问事端,我勉强作答。
“疯知青,到底给她吃了啥?”
“萝卜白菜煮青蛙,还有黄鳝。”
“白菜萝卜,是偷社员地里的吧?”
“要说饭里有毒,我咋没事儿呢?”
看着大家猜测的眼神,听着女知青的痛苦呻吟,我不禁哀从心起。这个漂亮的女人呵,可惜徒生其表,内心却如此脆弱——相爱不成也就算了,怎么会毒杀她呢?而且情节诡异,不由我妄加揣测此事的缘由:或因为所爱的女人将要离去,我因失爱而生恨,便走了极端;或由于她考上大学,我成绩更好反而落选,我因嫉妒而杀人。
这真是太滑稽了。若论情感纠葛,反倒是她为情所困,远甚于我;若为妒忌也说不通,投毒死一人就是了,我何必与她共食。这究竟怎么回事儿?我想得头晕,又瘟鸡似的抬眼望天。那会儿月明星疏,一只鸟儿在夜翔,不知要去哪儿。我仿佛坠入了人性的深渊。
事情闹到大半夜,干部社员早已散去。地窝外的月光给大地镀了一层银,看似很美,其实让人觉得阴森。杨百合呆看夜色,做解释:“我以为你恨爱不成,就一起殉情。可是我得回去呀!我妈妈在病中等我。所以,一切都请你原谅。就算不是爱情,在我最艰难的时候,是你给了我安慰,你也遭遇了痛苦。天禹你是我终生难忘的人……”
女人呜呜地哭了,我还能说什么呢?鄙视她、可伶她,还是反省自己。就本质上说,我们的整个情分,因由时局所限,也就是有欲而无爱罢了。我们就此了断情缘,实在说也正当时候,何况她还提到“殉情”二字,那可是男女之爱的最高境界。第二天,杨百合搽干眼泪,对着小镜子打理了一下,拎着行李上路了。临别时,她说要给我写信,其实一直没写。直到后来有一天,我俩在成都街头偶然相遇,又延续了许多其他故事。
既然说故事,就在杨百合走后不久,我的老友吴晓春忽然来到史安坪。他病青留城一直没工作,闲得无聊跑到农村来看我。晓春是懂音乐的,居然并凑了一个知青乐队。此事在当地闹得鸡犬不宁,却也是闻名遐迩。
下一篇
适合属蛇的同事属相